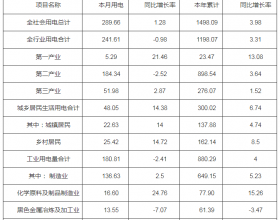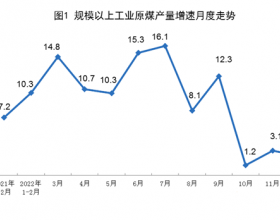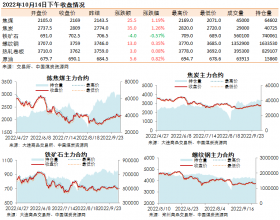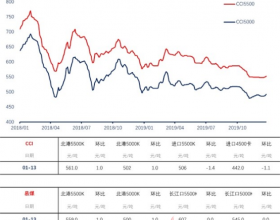记者了解到,此次“碳排放交易试点”并非一项全新的措施,2009年,该试点曾与财政部提出的《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方案并行讨论,但后者由于被认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而搁浅。
此次“碳排放交易试点”的正式展开,一方面被视为碳税政策的“打折”实施,一方面也被看做是为未来征收碳税做准备。
试点先行
据记者了解,“碳税方案”和“碳排放交易”方案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现行的发展战略,适用于不同的征收对象,碳税的实现路径是先进行成品油税费改革,然后推进资源税改革,最后推出碳税。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形成,对于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来说,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企业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
对于3年前的讨论为何最终选定“碳排放交易”先行,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认为是“迫于经济通胀压力,碳税方案实施条件不成熟”。
而对于上述7个省市被选中,刘桓指出,是与这几个地区的整体发展战略有关,这几个城市的节能减排需求比较大,碳排放指标大。
据记者了解,深圳、重庆也正在筹建交易平台,打算采取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配的碳交易试点模式。
行业影响有限
“我国目前碳市场的发展则处在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尚未明朗的特殊时期,尽管欧盟一再表明其坚持发展区域性碳市场的态度,但是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信用是否可以继续合法交易却存在诸多质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说。
业内人士也指出,在缺乏强制性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志愿性碳排放权交易不确定性非常大,无法形成有效稳定的市场。
一般认为,我国在资源环境管理领域的实践时间较短,一直以来主要集中于区域性污染控制,对于温室气体排放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则缺乏最基础的能力建设、制度设计和市场培育。
“碳排放交易试点可能采取和澳大利亚一样的模式。”刘桓告诉记者。
被称为最符合中国模式的“澳大利亚模式”,指的是“碳税+碳市场”的两阶段碳价机制,即前期为固定价格阶段,设定碳起始价,每年按实价递增2.5%。
第二阶段为排放交易机制,碳价由交易市场决定。碳市场用户包括固定排放源、交通、工业生产、废弃物(不允许丢弃)和不明排放源。
对于很多人担忧碳交易有可能加大企业负担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表示,多数试点省市均在过渡期内为重点行业设置了“免费配额”,先参与试点的企业可以有充足时间进行技术改造,今后碳排放配额用不完时,就成为碳交易的“卖方”,并从“买方”企业获得收益。
“对于试点城市而言,促成当地企业参与排放权交易也许并非最迫切的任务。”吴力波告诉记者,通过探索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明确总量约束目标的设定机制、初始排放权的分配机制、排放主体的参与机制、排放行为的监管机制、市场泄露的规避机制等五大因素,才是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通过市场化的交易真正实现社会总减排成本的最优化的关键所在。